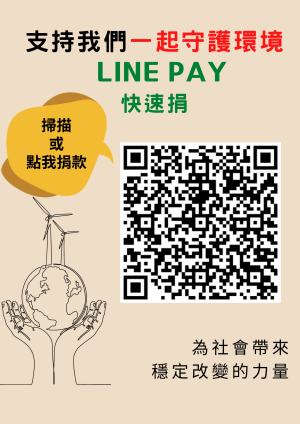【新任秘書長報到】看似偶然,其實也是必然
您在這裡
 我與主婦聯盟幾次相遇
我與主婦聯盟幾次相遇
1990年初,正值台灣各地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,大三的我第一次在課堂上聆聽了主婦聯盟董事的實踐分享。在研究所期間參與了多次反核四、倡導教改的遊行,有機會以不同角度理解主婦聯盟行動媽媽群的想法。後來我與十多個女性友伴共同發行獨立小刊物「圓仔花」,儘管此刊物是為了底層女工的勞教,但能理解辛苦的女工其實也都是媽媽,她們所思所想都是以家庭與社區為整體的系統觀點,所以逐步將家事與環境議題帶入文章中,以貼近婦女的真實經驗。
1997年,作為一個主跑地方社團與NPO的雜誌記者,我有幸來到主婦聯盟的辦公室,與當時的董事長暢談了一個多小時。當時她分享了女性力量應該集結於社區的理念,以及自己從社區出發一路上的轉折與人生風景。談話中有一段「風與太陽競賽」的童話故事:風的強勁與日光緩緩加熱的溫度,究竟哪一個發揮了真正的效用?她溫柔而堅定的相信,女人的力量與作法即是陽光。這一次的採訪如沐春風,點醒了年輕急躁的我,很多改變是在生活現場中慢慢細緻地做、點滴穿透出來的,這才是從多數女性主體經驗出發的社會行動策略。
一直到懷孕、生女,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,我才有機會落實在生活中實踐改革的理念。自2003年開始,我是主婦聯盟的合作社社員,與鄰居組成共同購買的一個班,常跑新竹「好所在」據點,閱讀每期「綠主張」,以原不熟悉的微觀視野重新看待自己陪伴孩子、家與周遭環境的關連性。不同於之前慣以大行動介入公共議題,我的小革命根植於自己每日吃了、用了、做了什麼的細節,必須誠懇面對伴隨母職而來的掙扎、便利的誘惑與資源有限性來進行自我對話。這些經驗相對輕盈不沈重,卻因真實深刻而自然成了日後家庭生活中的主調。
從觀念的刺激、視野的啟蒙,到領略實作經驗上的各種滋味與改革可能,不只是認同,我花了很多時間慢慢內化主婦聯盟所倡導的環保與綠色消費價值。
從社會運動、教育到的ngo實踐經驗
然而,要鼓起勇氣進到基金會裡工作,卻是在不同領域的職場裡累積與繞了一大圈之後,才又來到了這裡。
念研究所時,可謂熱血與青春無敵。除了積極參與婦女運動,上街頭為各種議題吶喊外,我也成為全景基金會紀錄片拍攝的學徒,期許以攝影機為弱勢的花東原民部落發聲;同時,以平溪、瑞芳與石碇等為基地,有一年半的時間也在煤礦社區裡蹲點學習與訪調,探究礦區勞動經濟與社區文化,並直接投入天主教敬仁勞工中心工作,為罹患塵肺症職業病的老礦工們爭取醫療與勞動權益。這些社會實踐與社區遊走,厚實了我與不同社群連結的能量,也觸探更多台灣社會生活的文化底蘊。
畢業後,遠見雜誌的記者工作,讓我可以對地方社區與社會力繼續關注,近距離理解生猛有力的社會運動團體逐步轉型為非營利組織,報導其如何在地、穩定而持續性的社會改革工程。
之後在新竹教書的十餘年,除了參與在地社區營造與教育訓練外,在校則負責「婦女福利」、「社區組織發展」與「非營利組織」等課程教學。但我總是不斷思索著不同女性在她們的真實生活中,聲音如何被聽見,如何打落牙齒和血吞地度過艱難的生命歷程,如何協同一起建構更緊密的社會支持網絡及社區參與,以邁向美好生活與社會平權的未來。因此,我訪問園區科技女主管母職的經驗,研究不同女人的社會記憶,探討社區保母制度的社會信任基礎,穿梭於新竹、桃園社區擔任志工訓練講師,也耐心培植一批批學生走向地方草根團體,進入921石崗災區、進入新竹縣市社區實作學習,與志工媽媽一起為社區照顧服務與社區產業發展尋找對策。
儘管在記者與大學內任教的生活相對安穩,體認教育工作之重要,也仍持續與許多非營利組織保持互動,但隨著女兒的成長與獨立,2012年初我決定跨出原有的經驗,因緣際會來到婦女團體,從事慰安婦與國際女性人權館的規劃,以及倡議、教育的工作。
看似偶然,其實也是必然
許多人問我,怎麼中年了,還有勇氣跳到環保團體工作呢?其實有許多理性版的答案,但最近腦海中最常出現的,卻是2001年在英國進修時,與好友一起到學校附近的社區遊行,舉牌抗議附近的農場裡偷偷種了基改玉米的畫面;還有大學畢業後那年冬天,跟著王俊秀老師來到南投鹿谷鄉進行垃圾考古,一袋一袋拆家用垃圾時的冷冽空氣與自己的雙手……。
既然這些片片段段的生命記憶自己就跳出來了,又是如此鮮活,我想,一切看似偶然,其實也應是必然。喜歡一段時間就跳開舒適圈的我,或許在許多轉換過程中累積了一些能力,也認識了許多人,遇見許多事,然後,時候一到,就自然來主婦聯盟報到,與大家歡喜相遇了!